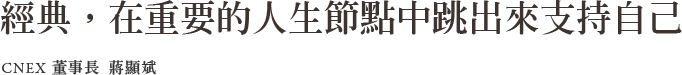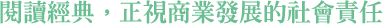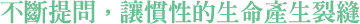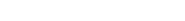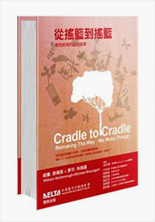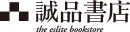我一直覺得我們這個世代是卡在中間的世代。我們面對的是脫離傳統觀念束縛之後,自己所要追求的價值到底在哪裡,所以會一直去看一些跟存在主義相關、跟新時代相關的書,試圖從這裡面找到答案。
無論你到哪一個國家留學,或是到了哪一個人生階段,在重要的人生節點時會跳出來的那本書,它是會一直跟著你的。這次問我要挑哪些經典,第一個從腦海跳出來的是跟我現在工作有關的,然後我再深入一點想,我目前的信念到底跟哪些書有關?
因此,從現在開始我們不得不正視,我們所有的設計者都要來思考「從搖籃到搖籃」的必要性。它也是一個向現在的科技和商業文明發出的挑戰書,但這個挑戰其實非常非常的難,我們現在所有的商業跟科技已經綑綁成一個牢不可破的慣性,你要去打破它並產生一個新的製造循環體系,成本通常就會比較高。但對於一個公司的決策者而言,較高的成本就必須要考慮到在商業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這也就考驗到所有消費者,對於用比較高成本,但比較有地球跟社會責任的產品,是不是有一個對價關係?這裡面展開來就變成整個商業系統跟科技系統之間非常難解的多元聯立方程式。
 我與《最初與最後的自由》、《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的淵源,是在大三的時候先看了《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它害我沒有準時畢業。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相當理性的,我的母親在輔仁大學營養系教書、我的外公在政府負責農業相關的工作,都是屬於比較理工思維的人,而這本書給我自圓自滿的人生系統產生一種裂縫,這個裂縫出現了以後,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線索就滲透進來了。
我與《最初與最後的自由》、《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的淵源,是在大三的時候先看了《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它害我沒有準時畢業。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相當理性的,我的母親在輔仁大學營養系教書、我的外公在政府負責農業相關的工作,都是屬於比較理工思維的人,而這本書給我自圓自滿的人生系統產生一種裂縫,這個裂縫出現了以後,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線索就滲透進來了。
因為書一直問你一些問題,我們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大學的時候它突然給了我一棍子,我發現原來這世界的可能性還有非常多。我那時是比較早開始在做技術性延畢的人,那時候大部分的同學都來關心我,我說沒有關係我很高興,因為我多了一年可以去補充很多沒有接觸過的領域。它和我後來做紀錄片其實是有關的。紀錄片的精神,並不是說我播一小時的紀錄片,就可以告訴你答案就是那樣,那叫宣導。現在的紀錄片其實提供給你的是幫你問問題,答案呢,由你自己去決定。紀錄片就像這些書,其實都是幫忙問問題的,它迫使你去問不能問的問題。我有時候覺得很多答案你找不到,是因為你問問題的方法不對,所以如果要訓練自己問問題的方法,這是一本非常棒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