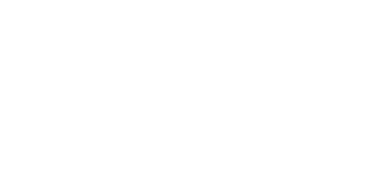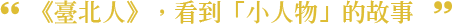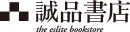攝影 / 簡尹益
攝影 / 簡尹益
過去我們上歷史課時得把書本內容背得滾瓜爛熟,很清楚台灣史、民國史的脈絡,但課本教的是大歷史,大人物的歷史。當時沒有閱讀課外讀物的概念,只能不停背誦課本裡的文字,如果《臺北人》放在那種地方,讀起來意義全然不同。但閱讀一本書的時候其實有很多角度,事實上可能連白先勇都不清楚他的角度為何。即使作者都有自己沒看到的角度,要由別人來看,但假使你把它當成考試的選擇題,我們又要用誰的角度來看呢?
後來,我習慣去閱讀小人物的故事,像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張戎的《鴻》,都是從小人物的故事去反映大歷史。第一次看《臺北人》時我大概三十歲,已經是大直高中的老師,發現《臺北人》也是在講這些小人物的故事,並且擁有更多不同的感觸。我們可以從開門頁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理解到,《臺北人》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他們會去懷念過去的美好,此外白先勇某程度上也是在講自己的故事,他的父親白崇禧到台灣後也幾乎過著被軟禁的生活,一個過去叱吒風雲的將領,晚年鬱鬱寡歡,他自己的家族,就是這樣的舊時門前燕,到台灣後便飛入尋常百姓家。他能把這些東西寫得如此漂亮、清楚,一定是用他從小到大身旁的親戚作為藍本,不然無法寫得這麼傳神。
第一次看《臺北人》時,因為書中寫了許多十里洋場,霞飛路的事情,便跑去上海,而且死都要去外灘領略那種感受。當時腦中畫面就是那種紙醉金迷、大官貴婦上流階級的生活。後來重讀,這段時間因為台灣政治與社會局面的轉變,讓我加深了對這些族群的共感。像書中這些人,若問他是哪裡人,他們幾乎都會說自己是中國人,他們人生的輝煌時期大部分都發生在中國,這對他們很自然。可是我在高中做民調時,問了五個班約兩百名學生,沒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樣的氛圍若是成型,書中那些人會更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更加深他們的被剝奪感。若要說從第一次閱讀這本書,到現在中間不斷閱讀時所感受到的差異,我會說自己希望能對他們抱持更多的同理心,有了同理心後,在從事社會運動時,才不會彼此傷害,這也是我閱讀《臺北人》的目的所在。即使他們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也不應該說他是錯誤的,在他人生的歷程中,確實有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理由,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時,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間點,台灣確實是中國的一部分。我一直不希望造成這樣的對立。
採訪 / 杜唯甄.整理 / 威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