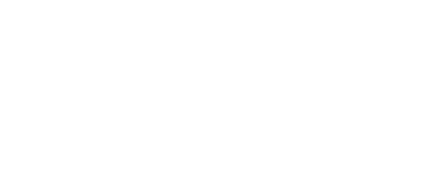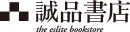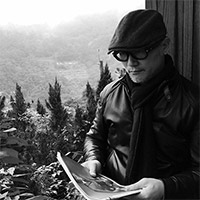 照片提供 / 高翊峰
照片提供 / 高翊峰
我讀卡繆的第一本書,便是《鼠疫》。那應該是在一九八八年。目前家中書架上,除了日前出版的《鼠疫》(麥田)之外,在過去零碎的時光裡,還有《瘟疫(黑死病)》(志文版)、《黑死病》(華美版)、《瘟疫》(遠景版),一共四本。
同一本書,陸陸續續買了四種不同的版本,其實也是自己重讀小說的方法。買了新的版本,便試著找時間再看過一遍。回憶這個作家的這本小說,同時也反問,這個故事對於不同時間的自己,具備了何種姿態,更新了哪些視角。
重讀卡繆的《鼠疫》,我反覆會想到的問題之一是:還活著的人,是怎麼看此時此刻,以及這個世界?最近一次,我給自己的答覆是:「⋯⋯排除數字之後,剩餘的都是還活著的倖存者,那些未感染與可能感染的集體他者,他們看見的對方,以及對方眼中的自己,構成了末日的面土。而埋入其中的,死者,是無權觀賞末日餘生的。」 但是,真的如此?首先,可以再進一步思考:末日,本身是一種什麼樣的情狀?
一杯冷了的咖啡,還能困住什麼?一杯隔夜的水割威士忌,能保存下時間感?順著一串的接連跳出來的提問,我反向想著,咖啡不只是咖啡因,威士忌也必然是大於酒精與品飲紀錄的。這也意味著,小說有機會大於活者,而活著可以不只是眼睛看見的那樣。這是卡繆這位小說家的小說作品,給我的感覺。如此搖晃迂迴的回到起點,「重讀」這件事,不應是驗證經典的方法,該是靠近可能經典的過程吧。但這類的討論,我依舊有著徒勞感。就像面對末日的思索,有著封閉情狀,是一樣徒勞的終感。
卡繆之於我,不只是閱讀上的意義而已。對於我個人的書寫,《鼠疫》這部小說中某種空間的封閉,其實具有某種十分幽微的定錨作用。我想,這也反照過去自己寫的兩部長篇小說《幻艙》與《泡沫戰爭》。前者的故事發生在「無法找到出口」的封閉地下室;後者的小說空間,則發生在一處「被孩童軍團封閉」的山中社區。我過去思考過「封閉」的意義,不僅在小說的介面,而是更真實的日常:活著,不就是一個完整空間的封閉。我也經常再向內探索,活者,也是一段封閉的時間狀態。如此而已,不會更長,但也不會更短。於是,一場鼠疫帶來的末日,不再是重點,而是封閉情狀下,我與各位都還耽溺其中,並且共同活著。
接著需要追問,彼岸那邊,有什麼樣的輪廓?《鼠疫》這部小說在彼岸那邊留下了什麼輪廓?這個問題之於我的價值在哪?我如此向自己提問,應該是有意義的,對吧?
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不代表多數。但閱讀的共鳴也好,創作的命題也好,其實都是小眾的。所以,我試著重複與重讀,最近一次我個人獨處的彼岸末日:「《鼠疫》指涉於我個人的悲願──只有活者才會擁有餘生;也只有活者需要睜眼,凝視末日的微小景觀。」
撰文 / 高翊峰